
陈骏教授:抗生素对恶性肿瘤患者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
恶性肿瘤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全球性问题,肿瘤与免疫系统的关系极为复杂,肿瘤免疫疗法通过强化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调动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和抑制其增殖,在多种肿瘤治疗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成为多种恶性肿瘤重要的治疗方法,可显著改善肿瘤患者的总生存率,然而相当一部分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不能获益。由于严重的免疫抑制和对传染病的易感性,癌症患者经常服用预防性抗生素。一些研究表明短期/长期使用抗生素与癌症风险增加之间存在关联。近来研究发现,人体菌群可能通过代谢、炎症或免疫等途径影响着恶性肿瘤的发生,肠道菌群与肿瘤免疫治疗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相关,抗生素的使用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将对抗生素对恶性肿患者免疫治疗效果的影响做一综述。
关键词:抗生素 免疫治疗 癌症 肠道菌群
作者:林美西 陈骏
陈骏
#1 前言
自从20世纪初抗生素的发现,特别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 之后,抗生素治疗的应用已经在全世界推广开来,毫无疑问,抗生素是过去100年人类和动物医学中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然而,抗生素治疗的一些消极方面在过去20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主要体现在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性增加,新的抗生素开发困难以及抗生素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相关性。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免疫治疗的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但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否受益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抗生素的不当使用造成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患者机体的代谢,免疫反应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因此指导恶性肿瘤患者合理使用抗生素具有很大意义。
之后,抗生素治疗的应用已经在全世界推广开来,毫无疑问,抗生素是过去100年人类和动物医学中最重要的药物之一。然而,抗生素治疗的一些消极方面在过去20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主要体现在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细菌耐药性增加,新的抗生素开发困难以及抗生素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相关性。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免疫治疗的价值和地位日益凸显,但治疗过程中患者是否受益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也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抗生素的不当使用造成的肠道菌群紊乱对患者机体的代谢,免疫反应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免疫治疗效果,因此指导恶性肿瘤患者合理使用抗生素具有很大意义。
#2癌症免疫治疗进展
2.1 免疫治疗的应用
2.1.1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近年来,大量的临床试验证实,与传统癌症治疗方式相比,免疫治疗具有更好的疗效,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 CTLA-4)为靶点的治疗方法在各种癌症患者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持久临床反应率。肿瘤组织限制宿主免疫反应的一个机制是通过上调PD-1配体(PD-L1)及其与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上的PD-1连接(称为适应性免疫抵抗)[1]。PD-1隶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CD28/B7,是由288个氨基酸 组成的Ⅰ型跨膜糖蛋白,为免疫抑制性受体,PD-1与PD-L1结合时,通过发生磷脂酰肌醇
组成的Ⅰ型跨膜糖蛋白,为免疫抑制性受体,PD-1与PD-L1结合时,通过发生磷脂酰肌醇 -3-激酶的磷酸化、蛋白激酶B的进一步激活、刺激性T细胞信号通路的活化、葡萄糖
-3-激酶的磷酸化、蛋白激酶B的进一步激活、刺激性T细胞信号通路的活化、葡萄糖 代谢以及干扰素的分泌等,导致T细胞活化的下游信号受阻,进而有效抑制T细胞的转录,最终抑制T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免疫应答的负性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可使T细胞活化上调,激活内源性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发挥对肿瘤的治疗作用[2]。CTLA-4是一种白细胞分化抗原,是T细胞上的一种跨膜受体,与CD28共同享有B7分子配体,而CTLA-4与B7分子结合后诱导T细胞无反应性,参与免疫反应的负调节。基因重组的CTLA-4 Ig可在体内外有效、特异地抑制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对移植排斥反应及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显著的治疗作用,毒副作用极低,是目前被认为较有希望的新的免疫抑制药物。
代谢以及干扰素的分泌等,导致T细胞活化的下游信号受阻,进而有效抑制T细胞的转录,最终抑制T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免疫应答的负性调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阻断PD-1/PD-L1信号通路可使T细胞活化上调,激活内源性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发挥对肿瘤的治疗作用[2]。CTLA-4是一种白细胞分化抗原,是T细胞上的一种跨膜受体,与CD28共同享有B7分子配体,而CTLA-4与B7分子结合后诱导T细胞无反应性,参与免疫反应的负调节。基因重组的CTLA-4 Ig可在体内外有效、特异地抑制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对移植排斥反应及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显著的治疗作用,毒副作用极低,是目前被认为较有希望的新的免疫抑制药物。
2.1.2 免疫治疗不良反应
自从2014年9月批准帕博利珠单抗 (Pembrolizumab)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3]以来,PD-1/PD-L1抑制剂作为抗癌药物的临床运用领域逐步扩展至从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Pembrolizumab)用于治疗晚期黑色素瘤[3]以来,PD-1/PD-L1抑制剂作为抗癌药物的临床运用领域逐步扩展至从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到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等多种癌症。其中,对于晚期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4]和肾细胞癌
到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等多种癌症。其中,对于晚期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4]和肾细胞癌 (Renal Cell Carcinoma,RCC)[5],抗PD-1抗体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但是只有约20%的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的长期生存期长达10年,越来越多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使用,暴露了一组独立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有些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免疫相关副作用,从而导致诸如肺炎、心肌炎
(Renal Cell Carcinoma,RCC)[5],抗PD-1抗体表现出显著的疗效。但是只有约20%的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的患者的长期生存期长达10年,越来越多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使用,暴露了一组独立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有些患者会出现严重的免疫相关副作用,从而导致诸如肺炎、心肌炎 或肝炎等有害后果[6]。仍有60-70%的患者存在原发性耐药[7],耐药的机制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包括肿瘤细胞对T细胞本身的作用具有内在的抵抗,由于缺乏肿瘤免疫原性而导致的T细胞浸润不足,宿主CD8+T细胞不能定位于肿瘤,或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局部免疫抑制因子,如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调节性T细胞(Treg)等[8]。而抗PD-1/PD-L1治疗获得性耐药的机制可能包括T细胞功能的最终丧失、抗原呈递中断,以及对T细胞产生的干扰素的抵抗等。此后,研究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影响PD-1/PD-L1抑制剂疗效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在治疗前表现出肿瘤微环境中持续的内源性T细胞反应的患者更容易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获益,控制这种表型存在与否的机制尚不清楚。肠道微生物群在形成全身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癌症领域,肠道微生物群在介导免疫激活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共生菌群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抗肿瘤的自发免疫反应,从而影响免疫治疗干预措施(如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的治疗活性。
或肝炎等有害后果[6]。仍有60-70%的患者存在原发性耐药[7],耐药的机制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包括肿瘤细胞对T细胞本身的作用具有内在的抵抗,由于缺乏肿瘤免疫原性而导致的T细胞浸润不足,宿主CD8+T细胞不能定位于肿瘤,或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局部免疫抑制因子,如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s),调节性T细胞(Treg)等[8]。而抗PD-1/PD-L1治疗获得性耐药的机制可能包括T细胞功能的最终丧失、抗原呈递中断,以及对T细胞产生的干扰素的抵抗等。此后,研究者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影响PD-1/PD-L1抑制剂疗效的影响因素。临床上,在治疗前表现出肿瘤微环境中持续的内源性T细胞反应的患者更容易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中获益,控制这种表型存在与否的机制尚不清楚。肠道微生物群在形成全身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癌症领域,肠道微生物群在介导免疫激活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共生菌群的变化是否会影响抗肿瘤的自发免疫反应,从而影响免疫治疗干预措施(如抗PD-1/PD-L1单克隆抗体)的治疗活性。
2.2 肠道菌群与癌症免疫治疗
肠道微生物群在维持机体内环境平衡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宿主能量代谢、肠道上皮通透性、肠道肽激素分泌和宿主炎症状态。正常菌群细胞壁的成分如肽聚糖、磷壁酸、多糖等经试验证实具有一定的抗肿瘤活性。微生物失调在肿瘤发生中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肠道微生物群影响局部和全身炎症,炎症对癌症的发展、进展和治疗均有影响,但目前尚不清楚共生细菌是否影响无菌肿瘤微环境中的炎症。2013年,ViaudS等和IidaN等[9]发现,在小鼠模型中,无菌或用抗生素杀死革兰氏阳性细菌的荷瘤小鼠显示pTh17(“pathogenic” T helper 17)反应降低,并且肿瘤对环磷酰胺 有耐药性。过继转移pTh17细胞部分恢复了环磷酰胺的抗肿瘤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微生物群有助于形成抗癌免疫反应。Iida N等人[10]发现微生物群的破坏损害了皮下肿瘤对CpG寡核苷酸免疫治疗和铂类化疗的反应。在接受抗生素治疗或无菌的小鼠中,肿瘤浸润性髓源细胞对治疗反应不佳,导致CpG寡核苷酸治疗后细胞因子生成减少和肿瘤坏死,化疗后活性氧生成不足和细胞毒性降低。因此,对癌症治疗的最佳反应需要一个完整的共生菌群,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中的髓源性细胞功能来调节其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微生物群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性。肿瘤相关炎性细胞促进癌细胞增殖,抑制抗肿瘤免疫。抗癌治疗改变了这种微环境,并可能引起破坏性免疫反应。实体瘤的T细胞浸润与良好的患者预后相关,然而个体间可变免疫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Sivan等人[11]比较了黑色素瘤在有不同共生菌群的小鼠体内的生长情况,并观察了自发抗肿瘤免疫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同居或粪便移植后被消除。16S核糖体RNA测序证实双歧杆菌
有耐药性。过继转移pTh17细胞部分恢复了环磷酰胺的抗肿瘤作用。这些结果表明微生物群有助于形成抗癌免疫反应。Iida N等人[10]发现微生物群的破坏损害了皮下肿瘤对CpG寡核苷酸免疫治疗和铂类化疗的反应。在接受抗生素治疗或无菌的小鼠中,肿瘤浸润性髓源细胞对治疗反应不佳,导致CpG寡核苷酸治疗后细胞因子生成减少和肿瘤坏死,化疗后活性氧生成不足和细胞毒性降低。因此,对癌症治疗的最佳反应需要一个完整的共生菌群,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中的髓源性细胞功能来调节其作用。这些发现强调了微生物群在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性。肿瘤相关炎性细胞促进癌细胞增殖,抑制抗肿瘤免疫。抗癌治疗改变了这种微环境,并可能引起破坏性免疫反应。实体瘤的T细胞浸润与良好的患者预后相关,然而个体间可变免疫反应的机制尚不清楚。Sivan等人[11]比较了黑色素瘤在有不同共生菌群的小鼠体内的生长情况,并观察了自发抗肿瘤免疫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同居或粪便移植后被消除。16S核糖体RNA测序证实双歧杆菌 具有抗肿瘤作用。口服双歧杆菌可使树突状细胞功能增强,导致CD8+T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启动和聚集,其程度与PD-L1特异性抗体治疗相同,两者联合治疗几乎可以消除肿瘤的生长。这些数据表明,控制微生物群可以调节癌症免疫治疗。另一种常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为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阻断剂。Vetizou等人[12]发现,CTLA-4阻断剂的抗肿瘤作用依赖于不同的类杆菌。微生物群的组成影响白细胞介素12(IL-12)依赖的TH1免疫反应,这有助于控制小鼠和患者的肿瘤,同时保留肠道的完整性。2017年,Jennifer AW等[13]则进一步研究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肠道菌群,研究显示对ICIs应答患者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显著增加,明显不同于对PD-1抑制剂无应答患者的肠道菌群。以上研究均提示,在小鼠模型中,肠道微生物组可影响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是全身性免疫反应的有效调节剂,不仅可调节化疗的疗效,而且可显著影响ICIs的抗肿瘤作用。
具有抗肿瘤作用。口服双歧杆菌可使树突状细胞功能增强,导致CD8+T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的启动和聚集,其程度与PD-L1特异性抗体治疗相同,两者联合治疗几乎可以消除肿瘤的生长。这些数据表明,控制微生物群可以调节癌症免疫治疗。另一种常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为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阻断剂。Vetizou等人[12]发现,CTLA-4阻断剂的抗肿瘤作用依赖于不同的类杆菌。微生物群的组成影响白细胞介素12(IL-12)依赖的TH1免疫反应,这有助于控制小鼠和患者的肿瘤,同时保留肠道的完整性。2017年,Jennifer AW等[13]则进一步研究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肠道菌群,研究显示对ICIs应答患者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显著增加,明显不同于对PD-1抑制剂无应答患者的肠道菌群。以上研究均提示,在小鼠模型中,肠道微生物组可影响局部和全身炎症反应,是全身性免疫反应的有效调节剂,不仅可调节化疗的疗效,而且可显著影响ICIs的抗肿瘤作用。
#3 抗生素使用对癌症患者的影响
3.1 抗生素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
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对其研究发现,一方面,抗生素可以直接靶向针对病原体,在抗感染治疗中起到选择性作用;另一方面,抗生素还可影响细胞毒细胞因子或下调炎症细胞因子及吞噬细胞氧化产物,在炎症性疾病中起调节作用。癌症患者常有多器官并发症。同时化疗和放疗会导致骨髓抑制,不能产生足够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抵抗感染,因此抗生素的使用不可或缺。随免疫调节的研究进展,目前的抗感染治疗不仅要考虑细菌的敏感性、抗菌能力和毒性,还要考虑抗生素的体内药效和对机体产生的免疫调节作用[14]。Bullman S[15]等表明梭杆菌与原发性结直肠癌 的远处转移持续相关,甲硝唑
的远处转移持续相关,甲硝唑 治疗可显著降低肿瘤组织中梭杆菌的负荷(P=0.002),并显著降低肿瘤细胞的增殖(P=0.002)。Zhang J等[16]证明口服抗生素的使用与结直肠癌风险有关,但其影响大小和危险类型因解剖位置而异。在任何抗生素使用中,结肠癌
治疗可显著降低肿瘤组织中梭杆菌的负荷(P=0.002),并显著降低肿瘤细胞的增殖(P=0.002)。Zhang J等[16]证明口服抗生素的使用与结直肠癌风险有关,但其影响大小和危险类型因解剖位置而异。在任何抗生素使用中,结肠癌 风险均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这种阳性关联与抗厌氧菌抗生素相关且仅限于近端结肠,然而在直肠中观察到,抗生素长期暴露降低了癌症风险。青霉素暴露与结肠癌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而四环素
风险均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这种阳性关联与抗厌氧菌抗生素相关且仅限于近端结肠,然而在直肠中观察到,抗生素长期暴露降低了癌症风险。青霉素暴露与结肠癌风险增加密切相关,而四环素 使用与直肠癌呈反比关系。Rosa CP等[17]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发现接受任何下尿路感染相关抗生素治疗的男性前列腺癌
使用与直肠癌呈反比关系。Rosa CP等[17]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发现接受任何下尿路感染相关抗生素治疗的男性前列腺癌 (PCa)的诊断风险增加19%(OR:1.19,95% CI:1.12–1.27),在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男性中,大多数接受过1到3次处方治疗。此外,甲氧苄啶
(PCa)的诊断风险增加19%(OR:1.19,95% CI:1.12–1.27),在接受过抗生素治疗的男性中,大多数接受过1到3次处方治疗。此外,甲氧苄啶 /磺胺
/磺胺 甲恶唑、环丙沙星
甲恶唑、环丙沙星 、强力霉素和诺氟沙星
、强力霉素和诺氟沙星 均与PCa风险增加相关,与未开处方的男性相比,在首次使用抗生素和PCa诊断之间有6-12个月时间的男性的相关性最强。癌症治疗中,抗生素的使用原因大多为预防用药、肺炎、呼吸道感染和尿路感染,然而,其导致的消极影响不可忽略。
均与PCa风险增加相关,与未开处方的男性相比,在首次使用抗生素和PCa诊断之间有6-12个月时间的男性的相关性最强。癌症治疗中,抗生素的使用原因大多为预防用药、肺炎、呼吸道感染和尿路感染,然而,其导致的消极影响不可忽略。
3.2 抗生素影响癌症免疫治疗
在一项大型多癌健康数据库调查中发现,服用青霉素的人患肺癌、食管癌 、胃癌
、胃癌 和肾癌的风险显著增加5倍以上。肺癌和肾癌的风险与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多个疗程显著相关[18]。Kim H等人回顾研究了2012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首尔圣玛丽医院接受ICIs(抗PD-1、抗PD-L1和抗CTLA-4单克隆抗体)治疗的234例各类型实体癌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包括单用ICIs、ICIs联合治疗和ICIs加化疗,而不考虑以前的抗癌治疗。在ICIs治疗开始前60天内,根据抗生素使用情况(是与否)对患者进行分类。对ICIs治疗前60天内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并对研究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与非抗生素组相比,抗生素组的疾病进展率(rate of progressive disease,PD)发生率更高,治疗客观有效率更低。抗生素使用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率(OS)均短于未使用抗生素组。此外,ICIs治疗期间使用抗生素与生存率无关,可能原因是首次给药引起的T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可能在此后持续存在。先前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发生在治疗开始后不到1周内,持续时间从1-3周至2年[19]。在多变量分析中,抗生素的使用是患者生存率的显著预测因子。证明了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影响ICIs治疗的实体癌患者的临床预后[20]。
和肾癌的风险显著增加5倍以上。肺癌和肾癌的风险与大环内酯类药物的多个疗程显著相关[18]。Kim H等人回顾研究了2012年2月至2018年5月期间在首尔圣玛丽医院接受ICIs(抗PD-1、抗PD-L1和抗CTLA-4单克隆抗体)治疗的234例各类型实体癌患者的病历。治疗方案包括单用ICIs、ICIs联合治疗和ICIs加化疗,而不考虑以前的抗癌治疗。在ICIs治疗开始前60天内,根据抗生素使用情况(是与否)对患者进行分类。对ICIs治疗前60天内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并对研究中最常见的癌症类型,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进行了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与非抗生素组相比,抗生素组的疾病进展率(rate of progressive disease,PD)发生率更高,治疗客观有效率更低。抗生素使用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率(OS)均短于未使用抗生素组。此外,ICIs治疗期间使用抗生素与生存率无关,可能原因是首次给药引起的T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可能在此后持续存在。先前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发生在治疗开始后不到1周内,持续时间从1-3周至2年[19]。在多变量分析中,抗生素的使用是患者生存率的显著预测因子。证明了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影响ICIs治疗的实体癌患者的临床预后[20]。
类似地,Ahmed等人[21]研究发现,与未接受抗生素的患者相比,接受广谱抗生素治疗的各类实体癌患者的有效率更低,总生存期(OS)较短,且PFS较短。Ueda K等人[22]采用回顾性分析发现,在80例接受抗PD-1/PD-L1抗体治疗的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的预后更差,癌症进展速度比未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更快。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在175名接受ICIs治疗的晚期肾细胞癌、尿路上皮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回顾性分析中得到同样的结果,与未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的中位PFS和OS显著缩短。
何姣等[23]通过meta分析评估了抗菌素对ICIs治疗NSCLC患者疗效的影响,发现 抗菌药暴露与OS、 PFS 的不良结果相关。抗菌药物的影响似乎取决于ICIs治疗药物种类、ICIs治疗开始前后抗菌药物的给药时间以及用药类型。亚组分析结果显示,抗菌素对单独使用PD-1治疗患者的OS影响较大,对以不同方式联合使用过PD-1、PD-L1、CTLA-4患者的PFS影响较大,而对PD-L1治疗组的OS、PFS无影响。
3.3 抗生素影响肠道菌群组成
肠道微生物群的破坏会影响全身T细胞活性及其数量,同时还会损害树突状细胞迁移、免疫球蛋白水平和干扰素γ水平。以前的研究报告指出,头孢菌素和β-内酰胺/β-内酰胺酶 抑制剂(beta-lactam/beta-lactamase inhibitors,blblbli)调节了肠杆菌群落中硬壁菌、拟杆菌和蛋白细菌的组成[24]。氟喹诺酮在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其变化程度因使用的喹诺酮类而异[25]。芬兰的一份报告表明,儿童食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变化,减少了放线杆菌,增加了类杆菌和蛋白细菌[26]。Arboleya等人[27]报道,β-内酰胺类药物降低了早产儿
抑制剂(beta-lactam/beta-lactamase inhibitors,blblbli)调节了肠杆菌群落中硬壁菌、拟杆菌和蛋白细菌的组成[24]。氟喹诺酮在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其变化程度因使用的喹诺酮类而异[25]。芬兰的一份报告表明,儿童食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变化,减少了放线杆菌,增加了类杆菌和蛋白细菌[26]。Arboleya等人[27]报道,β-内酰胺类药物降低了早产儿 放线杆菌(包括双歧杆菌)的比例。在另一项研究中,氟喹诺酮类药物会对共生菌群造成副作用,与双歧杆菌比例降低有关[28]。而且,DerosaL等和RoutyB等进一步发现与未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相比,抗生素治疗组的肠道菌群的丰富度明显减少,尤其是Akkermansia 菌(Akk菌)明显减少[29]。在抗生素使用周期方面,最常见的抗生素治疗时间≥7d。在短时间抗生素暴露的很长一段时间后,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仍有持续的长期影响[30]。Liao W等[31]通过meta分析表明,在抗生素治疗期间尽早使用益生菌对预防成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放线杆菌(包括双歧杆菌)的比例。在另一项研究中,氟喹诺酮类药物会对共生菌群造成副作用,与双歧杆菌比例降低有关[28]。而且,DerosaL等和RoutyB等进一步发现与未使用抗生素的患者相比,抗生素治疗组的肠道菌群的丰富度明显减少,尤其是Akkermansia 菌(Akk菌)明显减少[29]。在抗生素使用周期方面,最常见的抗生素治疗时间≥7d。在短时间抗生素暴露的很长一段时间后,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仍有持续的长期影响[30]。Liao W等[31]通过meta分析表明,在抗生素治疗期间尽早使用益生菌对预防成人抗生素相关性腹泻 (AAD)具有积极和安全的作用。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可显著减少肠道菌群的细菌丰富度,导致其多样性、均匀性急剧下降,引起肠道菌群失调
(AAD)具有积极和安全的作用。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可显著减少肠道菌群的细菌丰富度,导致其多样性、均匀性急剧下降,引起肠道菌群失调 ,即组分和功能紊乱,导致对感染的易感性增加,进一步导致代谢失调和免疫稳态受损。
,即组分和功能紊乱,导致对感染的易感性增加,进一步导致代谢失调和免疫稳态受损。
#4 抗生素导致的肠道菌群变化与癌症治疗相关性
肠道菌群失调触发了许多与肿瘤形成过程相关的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肠道菌群的变化会诱导IL-6、GMCSF、TGF-β等细胞因子的产生,促进肿瘤炎症微环境的形成,同时增强(MDSCs)和(Tregs)向肿瘤微环境的募集,维持免疫微环境,在这些细胞的存在下,T细胞消除肿瘤的能力受到抑制[32]。研究表明,微生物群及其相关代谢物不仅通过诱导炎症和免疫失调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干扰抗肿瘤药物的药效学[33]。除了肠道菌群,肿瘤内的细菌本身也可能影响肿瘤的发展和治疗,可见,肠道菌群诱导癌变的机制可能包括炎症诱导、细胞信号改变和抑制免疫细胞的杀伤效应。刘秀等[34]通过对使用不同种抗生素的大鼠粪便进行收集和DNA提取及测序,证明抗生素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大鼠的肠道菌种数目(t=9.15,p<0.01)。在门水平分析大鼠的肠道菌群组成,结果显示,抗生素干预了大部分的肠道菌门,即Elusimicrobia、Cyanobacteria、Pro-teobacteria、Firmicutes、Verrucomicrobia和Bacteroidetes的 相 对 丰 度 都 发 生 显 著 变 化 (t=2.53-12.97,P,0.05)。
在小鼠模型中,接受PD-1/CTLA-4单克隆抗体的小鼠使用抗生素处理后抗肿瘤作用明显降低,但是经过移植对ICIs响应的患者粪便或喂服Akkermansia 菌(Akk菌)后,小鼠抗肿瘤作用均有所提高。Routy等人表明,在治疗前接受大便基因组学分析的患者中,粘液阿卡曼菌的丰度与抗PD-1免疫治疗反应相关。从ICIs应答者到无菌或抗生素治疗小鼠的FMT改善了抗PD-1单克隆抗体的肿瘤控制,而来自无应答者的FMT无法实现肿瘤控制。口服粘液棘球蚴和无反应者粪便的FMT通过在小鼠肿瘤微环境中累积CCR9+CXCR3+CD4+T淋巴细胞,恢复抗PD-1单克隆抗体的抗肿瘤作用[29]。Vétizou等人[12]将接种了 MCA-205肉瘤并接受 anti-CTLA-4 治疗的小鼠分为2组,在IL-10缺乏和CTLA-4阻断的情况下观察到破坏肠道菌群导致的结肠炎甚至可以对抗抗癌疗效,而补充脆弱类杆菌(Bacteroides fragilis)等菌种可以恢复部分anti-CTLA-4的治疗效果。由此可见,使用抗生素可影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实体瘤的疗效,使用抗生素可能是ICIs治疗的新型的独立预后因素。基于这些发现,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被认为可能改善实体癌患者的ICIs治疗效果。这些数据表明,抗生素作用引起的肠道菌群变化可能是导致ICIs疗效不佳的原因之一。有目的地调整肠道菌群使免疫治疗有益菌富集,有望成为提高免疫治疗疗效的手段[35]。
#5 总结
人体的肠道中有大量的细菌,较其他部位更易受到抗生素的影响,抗生素的使用破坏了原有的肠道菌群,从而产生相应的临床结果。肠道微生物群紊乱发生在定性和定量上。失调的特征是一种替代的微生物群状态,其中T细胞亚群、Th1、Th2、Treg以及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CFA)、抗体(尤其是IgA)和细胞因子发生改变。抗生素药物通常用于感染,也可以针对共生微生物群,使肠道菌群失调。重要的是,它们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剂量、时间和药物类型,而且还取决于肠菌中存在的不同细菌种类含量和多样性的靶点,从而影响宿主的健康和疾病的进展[36]。近几年一系列的研究都表明肠道菌群似乎在抗生素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效的关系中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但是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干扰因素,首先,与未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相比,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一般情况较差,相应预后也会较差;其次,不同种类抗生素的给药方式存在不同,口服与静脉给药,抗生素的腔内浓度也不同;最后,患者的情绪变化,生存环境,饮食规律并不统一,可能从多个方面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因此,需要对同质患者群体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现有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抗生素的使用可能会影响癌症患者行ICIs治疗的临床疗效。在必要时使用抗生素,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可能会改善计划接受ICIs治疗的患者的治疗效果。除严格选用抗生素,还需要进一步临床试验以明晰用药后患者肠道菌群的稳态变化,进而规范治疗策略,改善抗生素使用弊端,真正为癌症患者带来福祉。
专家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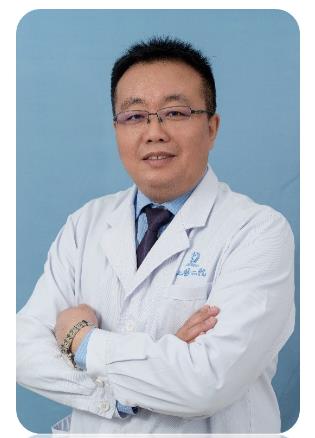
陈骏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胸部肿瘤1科主任
肿瘤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美国Mayo Clinic(梅奥医院)高级访问学者
澳大利亚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西澳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国际癌症支持治疗学会(MASCC)会员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会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分子肿瘤与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肿瘤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肺癌防治联盟液体活检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精准医疗分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抗癌协会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免疫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Tumeh PC, Harview CL, Yearley JH, et al. PD-1 blockade induces responses by inhibiting adaptive immune resistance. Nature. 2014 Nov 27;515(7528):568-71.
[2]赵秋玲,杨琳,谢瑞祥.9种获批上市的抗PD-1/PD-L1单抗药物的特征综述[J].中国药房,2020,31(18):2294-2299.
[3]Mahoney KM, Freeman GJ, McDermott DF. The Next Immune-Checkpoint Inhibitors: PD-1/PD-L1 Blockade in Melanoma. Clin Ther. 2015 Apr 1;37(4):764-82.
[4]Miyazawa T, Marushima H, Saji H, et al. PD-L1 Expression in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Including Various Adenocarcinoma Subtypes. Ann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9 Feb 20;25(1):1-9.
[5]Brahmer JR, Tykodi SS, Chow LQ, et al. Safety and activity of anti-PD-L1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N Engl J Med. 2012 Jun 28;366(26):2455-65.
[6]Puzanov I, Diab A, Abdallah K, et al. Managing toxicitie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consensus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Society for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SITC) Toxicity Management Working Group. J Immunother Cancer. 2017 Nov 21;5(1):95.
[7]Wang Q, Wu X. Primary and acquired resistance to PD-1/PD-L1 blockade in cancer treatment. Int Immunopharmacol. 2017 May;46:210-219.
[8]Nowicki TS, Hu-Lieskovan S, Ribas A.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o PD-1 and PD-L1 Blockade. Cancer J. 2018 Jan/Feb;24(1):47-53.
[9]Viaud S, Saccheri F, Mignot G, et al.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modulates the anticancer immune effects of cyclophosphamide. Science. 2013 Nov 22;342(6161):971-6.
[10]Iida N, Dzutsev A, Stewart CA, et al. Commensal bacteria control cancer response to therapy by modula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3 Nov 22;342(6161):967-70.
[11]Sivan A, Corrales L, Hubert N, et al. Commensal Bifidobacterium promotes antitumor immunity and facilitates anti-PD-L1 efficacy. Science. 2015 Nov 27;350(6264):1084-9.
[12]Vétizou M, Pitt JM, Daillère R, et al. Anticancer immunotherapy by CTLA-4 blockade relies on the gut microbiota. Science. 2015 Nov 27;350(6264):1079-84.
[13]Jennifer AW, V ancheswaran G, Christine S, et al. Association of the diversity and composition of the gut microbiome with responses and survival (PFS) in metastatic melanoma (MM) patients (pts) on anti-PD-1 therapy[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 2017, 35(15 suppl):3008–3008.
[14]黄静,张天托.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免疫调节分子机制研究进展[J].国外医药(抗生素分册),2006(05):211-215.
[15]Bullman S, Pedamallu CS, Sicinska E, et al. Analysis of Fusobacterium persistence and antibiotic response in colorectal cancer. Science. 2017 Dec 15;358(6369):1443-1448.
[16]Zhang J, Haines C, Watson AJM, et al. Oral antibiotic use and risk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89-2012: 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Gut. 2019 Nov;68(11):1971-1978.
[17]Rosa CP, Brancaglion GA, Miyauchi-Tavares TM, et al. Antibiotic-induced dysbiosis effects on the murin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their systemic repercussions. Life Sci. 2018 Aug 15;207:480-491.
[18]Boursi B, Mamtani R, Haynes K, et al. Recurrent antibiotic exposure may promote cancer formation--Another step in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the human microbiota? Eur J Cancer. 2015 Nov;51(17):2655-64.
[19]Derosa L, Hellmann MD, Spaziano M, et al. Negative association of antibiotics on clinical activity of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renal cell and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nn Oncol. 2018 Jun 1;29(6):1437-1444.
[20]Kim H, Lee JE, Hong SH, et al. The effect of antibiotics on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solid cancers undergoing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treatment: a retrospective study. BMC Cancer. 2019 Nov 12;19(1):1100.
[21]Ahmed J, Kumar A, Parikh K, et al. Use of broad-spectrum antibiotics impacts outcome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Oncoimmunology. 2018 Aug 20;7(11):e1507670.
[22]Ueda K, Yonekura S, Ogasawara N, et al. The Impact of Antibiotics on Prognosis of Metastatic Renal Cell Carcinoma in Japanese Patients Treated With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Anticancer Res. 2019 Nov;39(11):6265-6271.
[23]何姣,刘晓波,陈瑞祥,温瑾,赵倩,张清树.抗菌药物对非小细胞肺癌免疫疗效影响的Meta分析[J/OL].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10.
[24]Knecht H, Neulinger SC, Heinsen FA, et al. Effects of β-lactam antibiotics and fluoroquinolones on human gut microbiota in relation to Clostridium difficile associated diarrhea. PLoS One. 2014 Feb 28;9(2):e89417.
[25]Inagaki Y, Nakaya R, Chida T, et al. The effect of levofloxacin, an optically-active isomer of ofloxacin, on fecal microflora in human volunteers. Jpn J Antibiot. 1992 Mar;45(3):241-52.
[26]Korpela K, Salonen A, Virta LJ, et al. Intestinal microbiome is related to lifetime antibiotic use in Finnish pre-school children. Nat Commun. 2016 Jan 26;7:10410.
[27]Arboleya S, Sánchez B, Solís G, et al. Impact of Prematurity and Perinatal Antibiotics on the Developing Intestinal Microbiota: A Functional Inference Study. Int J Mol Sci. 2016 Apr 29;17(5):649.
[28]Stewardson AJ, Gaïa N, François P, et al. Collateral damage from oral ciprofloxacin versus nitrofurantoin in out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 culture-free analysis of gut microbiota.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5 Apr;21(4):344.e1-11.
[29]Routy B, Le Chatelier E, Derosa L, et al. Gut microbiome influences efficacy of PD-1-based immunotherapy against epithelial tumors. Science. 2018 Jan 5;359(6371):91-97.
[30]Jernberg C, Löfmark S, Edlund C, et al. Long-term ecological impacts of antibiotic administration on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ota. ISME J. 2007 May;1(1):56-66.
[31]Liao W, Chen C, Wen T, Zhao Q. Probiotics for the Prevention of Antibiotic-associated Diarrhea in Adult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J Clin Gastroenterol. 2020 Nov 23.
[32] Buchta Rosean CM, Rutkowski M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ensal microbiota on distal tumor-promoting inflammation. Semin Immunol. 2017 Aug;32:62-73.
[33]Meng C, Bai C, Brown TD, et al. Human Gut Microbiota and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Genomics Proteomics Bioinformatics. 2018 Feb;16(1):33-49.
[34]刘秀,吕秋兰,赵鹏,杨晓敏,徐大星,邢士超.抗生素短期干预所致肠道菌群紊乱对大鼠食欲和糖脂代谢的影响[J/OL].青岛大学学报(医学版):1-5
[35]锁娇娇,魏豪,汪燕,朱江.调节肿瘤免疫治疗的靶点:肠道菌群[J].中国肿瘤,2020,29(04):304-308.
[36]Rosa CP, Brancaglion GA, Miyauchi-Tavares TM, Corsetti PP, de Almeida LA. Antibiotic-induced dysbiosis effects on the murin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their systemic repercussions. Life Sci. 2018 Aug 15;207:480-491.
